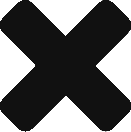下午四點48分,黯藍的天泛著玫瑰粉紅, 顏色交會之際是冬夜降臨前才會有的淺羅蘭紫,我彷彿看見了遠方準備升起的第一顆星。無法確定那是星星,還是從鄰近機場起飛的飛機。這裡的天好乾冷好暗沉,即使已經回來四天多了,我仍覺得我的靈魂仍遺落在台灣,還未追上已經回到賓州中中部的身體。冬天,賓州的黑夜降臨地好早。
一週前的今天,我去北投找外婆。自從去年外公在我離開台灣後一個月毫無預警地去世後,我時常擔心自己在海外來不及見到家人或朋友最後一面。原來講再多的未來與規劃、堆砌再多成就與光環,人生說到底就是生活點滴的組成,而生活中最讓人有立即感受的即是生老病死, 還有生死之間的各種別離與重逢。
還沒走到外婆家公寓門口,就看見外婆坐在樓下的修車廠旁等我,包著頭巾,握著傘柄,纖瘦的腳輕踩著水泥地,一時之間我竟認不出她來。
十一月的東北季風裡,外婆的肩與臂嶙峋脆弱,我扶著她過馬路,怕一不小心就將她給弄疼弄碎。「要不要去吃對面的水餃與酸辣湯?」 以為是她時常下樓散步,嚐過街坊邊的那間八方雲集,後來才從媽媽的口中得知,我去找外婆的前幾天,她特別跑去八方雲集「試吃」那裡的水餃與鍋貼,希望孫女來找她時,能有個周延的聚會。凡事求完滿、求工整,曾經有體力燒一桌好菜的外婆,在她再也沒有足夠體力的時候,仍然以她樸拙的方式,想要給出最好最好的。
一起走進店裡,外婆點了水餃和酸辣湯,我叫了鍋貼與豆漿,一方木桌與長板凳邊,我們坐看著店門外稀疏往來的人客。靜靜的四方小空間裡,就我們倆,還有前方忙著包餃子的阿姨們。外婆悠悠緩緩地說起了她年少時在第四十四號兵工廠當護士的故事, 故事我聽了幾回,有來自外婆的版本,也有來自媽媽的轉述。故事裡的外婆是個十多歲的女孩,聰明好學、寧靜溫順,深得同事以及負責兵工廠醫務的侯醫生夫婦的喜愛。女孩有很強的求知慾,醫生夫婦以及許多認識女孩的親友都很鼓勵她繼續升學。從來不記得故事的結尾,因為每一次外婆與媽媽的訴說裡,女孩對未來與知識的渴望無疾而終。故事的盡頭是年少婚姻,是媽媽,是我。
第四十四號兵工廠,殷勤的阿兵哥,從來沒有拆開過的情書,反共復國的大時代焦慮牽動著外婆的母親的擔憂神經。想像著女孩與外省籍阿兵哥在未來可能的孤苦生活,母親聽了嬸嬸的話,為女孩做了媒。
「剛結婚的時候很常跟你的外公吵架,負氣跑回娘家,又不敢讓爸爸媽媽知道發生什麼事,怕他們傷心覺得幫我做了爛媒,誤了我一生。有一次,吵得很嚴重,我說什麼也不回婆家,我爸爸背對著我哭了出來。」後來的故事,我們都知道,那個年代的做女人、做媳婦的能夠過得多好?只是,年輕的女孩怎麼會明白,自己被做的這個媒,其實也只是當年作為媒人的嬸嬸為了打擊另一個女人而使出的手段。女孩,良善單純,卻莫名其妙成為新家的婆婆最討厭的人。
女孩當年有許多事情不能告訴她的爸爸媽媽,後來成為母親,她的女兒也有許多不能告訴她的事,包括她自己的婚姻,她曾經日日夜夜遭受的恐懼,她巨大無可彌補的寂寞。水瓶裡似毒藥的白色粉末,裝滿貴重物品的行李箱,每天半夜空著一半的雙人床,缺愛的人生裡,孤寂地餵食與面對自己精神裡的魑魅魍魎。
女孩的女兒不能說的,我作為女兒的女兒,也只能把話語靜沉在心裏。看著被歲月洗滌的女孩,乳白柔軟的頭髮,我也只能點點頭,成全她對於自己的女兒嫁得好人家的幸福想像。
帶著許多未說完也不能說的話回來賓州,眼看這個年又快要過完了,冰天雪地,好是寂寥。都說要年年有餘,餘的是好運,是衣食與豐收。餘是盈滿,也是剩餘與殘餘,像是女孩走完四分之三個世紀老伴去世後的餘下晚年,像是女孩的女兒小心翼翼保護卻所剩不多的愛的能力。
年年有餘,當自己也遇到了另一個人,並且持續在無邊的生活與知識領域裡探索自己,我時常感覺自己拿了不屬於自己的運命。憑什麼我能這樣隨心所欲、愛己所愛,而在第四十四號兵工廠當護士的女孩還有她的女兒卻沒有福份享受?得己所得,也不是因為自己比較聰明,比較好,或許只是我消受了餘下的好運,像是被賜予了走在我前面的她們積累的、沒能享受的福份。
年年有餘,如果回來冰天雪地的美國東北不能過得隨心所欲之充盈,也還是想輕捧著交到我手裡的餘下的運命,靜默守望不能被說破的缺。拿著殘餘的,讓它變得充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