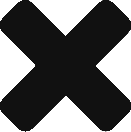星期天的早晨,吃完早餐,我們到附近的一處公園散步。原本只是想說看看濕地與山脈,認識一下附近的步道,沒想到卻邂逅了一個大鹽池。這個公園位在舊金山海灣的最深處,海水從狹窄的金門大橋灣口進來以後留下營養物與鹽,因而造成鹽分較高的濕地生態圈。漲潮時從海灣湧進乾淨的水源,退潮時潮汐又會帶走這裡的污染物,這裡的生態圈因而有足夠的土壤養分支持許多耐鹽的植物、水鳥。
第一次看見鹽池,鹹水映照著早晨的日光,水天一色的蔚藍很強勢地佔據我的心神,瞳孔裡只有無盡且廣闊的藍。那個時候,我覺得胸口特別舒暢,很想要好好記住那樣的感覺。
生活中的舒暢感,是進入成人世界裡以後的我很想要好好守護的東西。回想這一、兩年,電話裡與一同成長的朋友們的共同話題逐漸從單純的唸書與人際關係變成財務焦慮、健康、身份與居留、家庭,貸款與稅,當然還有每日瞬息萬變的職場環境——成長好像就是經歷生活一系列生理痛的過程。
從研究所畢業後進入職場也五個月了,雖然我很喜歡現在的工作與環境,卻也不時在思考每天將自己寶貴的八小時賣給體制與公司這件事情。 許多時候,我覺得我賣的不只是時間,還有我一天之中那寶貴且有限的專注力;下班以後的我,即使有多餘的時間,大腦偶爾還是會處在緊繃的狀態,沒有辦法像以前一樣看很多的文本、寫很多字。
我時常突發奇想地問君翊,有沒有可能不要上班、不要工作,自己種喜歡的蔬果,過一個不假外求、自給自足的生活?都還沒有講完,就會想到,在美國以及許多地方,工作綁著醫療保險與退休金,並且讓自己有能力去應付生活上的緊急事故。尤其在資本主義當道的年代,好像唯有工作,才能夠去享有社會帶來的基本照護,唯有工作,才能夠維持生活的基本所需,也才能夠融入社群。我享受工作場所帶給我的社交與歸屬感,卻也時常覺得要能夠不將自己工具化、以生產衡量自己的價值,需要非常強大的心靈能量。
最近偶爾讀《過度失控的努力文化:失控的努力文化:為什麼我們的社會讓人無法好好休息》這本書,作者 Celeste Headlee 從人類的生理構造、演化與工業革命前後的歷史等角度切入,諄諄告誡讀者一直追求生產力的行為模式是有害的。弔詭的地方就在於,即使我們知道我們正在傷害自己的身體,卻還是停不下來。Headlee 鼓勵讀者培養需要長時間專注的興趣,讓自己能夠在資訊爆炸、腳步加遽的社會裡停下來。那些回歸到我們身上的專注力,就像我們送給自己的禮物。
那個停不下來的失控感,好像應證了文化理論家 Lauren Berlant 所提出的「殘酷樂觀主義」(cruel optimism),講的是人們會帶著樂觀與希望去追求某些東西,即使那些東西本質上是對自己有所傷害的,例如讓自己停不下來的工作或是必須以極高代價去取得的光環。
我對於那種停不下來的感覺,既想要抵禦,也充滿同理。我們被教育著要去追求某種生活模式,追求頭銜與產出,那樣的教育無所不在。無論是正規教育、廣告、還是社群媒體,或者是同儕之間的壓力,那種思維一不小心就會成為我們吸進去的每一口空氣。
—
來到大鹽池邊,空氣裡充滿濕地與鹽分的味道,吹著港灣進來的風好像有心上有什麼東西被治癒的感覺。想要把這樣的感覺寫下來,明白能夠擁有一點自己的時間寫作,暫時不用擔心生活、工作以及各種瑣事,只是把僅有的專注留給自己是件多麼得來不易的事情。
雖然我可能永遠無法從體制裡出走,並且承擔越來越多的事情,但我想要記下在藏藍的池與天空下那倏忽即逝的輕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