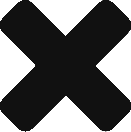在賓州的防疫隔離將近三個月了,三月中時還在猜測這樣的光景會不會持續到夏天或是更久以後,現在想起,當時覺得稀奇非常之物事,現在也變得平凡日常了。
過去這幾個月,內心經歷了許多動盪與改變,一方面參與著世界大眾的焦慮恐慌,另一方面又要繼續持續進行文學課堂,努力當一個傾聽者與保護者,直到課堂完全結束為止。看著每一天不斷新增的死亡與疾病案例,還有不斷攀升的失業人口、各式的財務緊縮,實在很難想像事情開始好轉的一天。就算「好起來」了,疾病本身以及各地失能政府造成的創傷,也要好幾年才能復原。沒有人能全身而退,只能思索著自己從災難另一頭出來時,會失去哪些東西,以及還能保有哪些東西。
過去這些日子像是夢一樣,在惡夢裡看著各種體制崩解,而體制裡脆弱的人繼續被剝削,原本就已經很狹窄、很緊縮的未來,現在幾乎已經快要看不見了。在這樣的惡夢裡,我想保有的是自己的創造力,那不依賴也不受制於體制的東西。於是我開始嘗試了許多自己不曾嘗試的事情:開始自學日文、讀《冰與火之歌》的小說、有計畫地書寫、探索附近個公園、山林步道。而我仍然持續閱讀著,在讀完石黑一雄《被埋葬的記憶》之後,我重讀了國中時讀的卡洛斯·魯依斯·薩豐的《風之影》,也重讀了李維菁的《人魚紀》,然後每一天一點點地,完成一直想為《人魚紀》寫的書評。
想起李維菁在《人魚紀》一書裡寫道的:「一個人有自己的秘密世界隨時可以進出,才能活下去,活得有尊嚴。」閱讀,大概就是我在不斷緊縮的現實裡的秘密通道,像是在涵養自己不能被資本邏輯、學術理論吸納的世界。在這裡,沒有什麼展演或是高談闊論,也無所謂工作與產出,暫別理論與批判的書寫,就只是一個字、一個字地讀。一種踏實。
前幾天,從台灣訂來的邱妙津的兩冊日記還有賴香吟的《其後》寄到家裡來了。在賴香吟為邱妙津日記寫的序裡,她提到邱妙津伏案寫日記的模樣,嚴肅專注,『宛若儀式的完成」,日記是邱妙津整理心緒的地方,誠實赤裸,豐沛熾熱,令人想起她在《鱷魚手記》與《蒙馬特遺書》裡的自剖。
讀著這些文字,聆聽不同的聲音,對我來說就像是為自己的靈魂取得某種程度的生存權一樣。過去這個月時常跟系上幾位好友通電話聯絡近況,我們最常聊的就是學術體制的層層剝削、權力不對等與情緒勒索,還有在這些腐蝕我們熱情的現實之中,成長茁壯的自己。從小在家裡,我就一直是個不想讓自己被看見的人,我很安靜,因為很害怕任何動作會引來父母的質疑、情緒崩潰跟勒索,我享受不被注意,享受消失。然而朋友們總是不忘提醒我,在這裡,我應該speak up,去察覺自己沒有被公正地對待,為自己發聲,時機適當時,也要讓人知道自己的底線。
劃清底線是最困難的,因為許多時候我們不僅不知道自己的底線是什麼,甚至因為害怕而一直去為體制裡的施暴者護航,否認別人的侵犯與傷害。
我覺得劃清底線需要相當程度的自愛,不知道為什麼我想到邱妙津在日記裡寫道,她立志成為偉大的藝術家,而她也知道自己的書寫離她所認定的藝術高度已經近了。我很佩服邱妙津那樣的想望,那不是自傲狂妄,而是對於自己的天賦的理解,對自己心之所愛的把持,在沒有眾人目光鞏固時,她已經先見證自己濃烈的情感與藝術高度。這樣的理解與把持,需要巨大程度的自我愛惜才做得到吧!
雖然我沒有那樣的情感與才賦,但卻相信藉由寫作、寫日記,細細琢磨一字一句與自己的心緒,終將能學會看見自己內在複雜與深度,進而愛惜自己。我們也不再輕易地讓生病的體制與體制裡的暴力塑造自己,奪走所剩不多的心力與時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