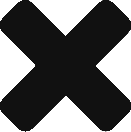收到學生的來信,說他這幾天還沒有領到錢無法買教科書,希望我能幫他。要怎麼幫他?要幫他掃描所有的指定閱讀呢?還是幫他找便宜的教科書買賣網站?還是把我的書借給他 (但這是線上課程,他人也不在鎮上)?還是隨便回了他的郵件,說我也沒辦法?
像這樣大大小小的抉擇,佔據了我過去三年的教學生活不少部分。這些抉擇困難的地方,並不是事物本身的複雜,而是我也必須衡量自己有多少能力與資源能夠幫我的學生。我也害怕跟學生太過親密,導致他們太依賴我、不尊重我,但我更害怕一不小心做錯決定、說錯話,傷害學生和他們對學習的熱情。親密與距離,時常又因為各種身份認同的標籤,像是種族、國籍、性別、年齡、階級、政治意見,而變得更複雜。在賓州州大的每一天,我都小心翼翼地遊走著每一個教學現場。
賓州州大就像美國大部份的州立大學一樣,位在一個地理位置孤立的大學城裡,四周是美麗平緩的山丘、玉米田、農場,我的學生大部份來自賓州的鄉下,或是賓州的兩座大城 (費城與匹茲堡)。由於位在東北地區較鄉下的地方,我的學生大約七成都是白人,大部份來自家境富裕的中產家庭。記得剛開始在這裡教書,看到各個看似自信滿滿的學生,我總無法停止思考世界賦予了他/她們多少特權,就只因為他/她們是美國公民,白皮膚,人們想像中的「第一世界」的光環在我的學生們的言談、舉止之間乍現。
一開始教書的時候教的是大一的寫作課,當時我也只比我的學生大三、四歲,對於教學還沒有太成熟的想像,希望能與學生打成一片。大部份的學生知道我是台灣人時,覺得很驚奇、很新鮮,也喜歡偶爾聽我碎念南島文化與風景。然而,偶爾還是會有學生對於亞洲臉孔的老師充滿防衛心與懷疑,雖然說不上是敵意,我卻知道自己時時刻刻被打量著。在學界裡待了一陣子,才理解了要在白人支配的世界裡,當一個有色人種的女性,無論是作為學者、研究員、或是老師,都是挑戰重重。
所謂挑戰不只來自體制上的各種天花板,也影響了作為有色人種的我們的自我認知與世界觀。我想起以前曾聽在比較文學系裡的老師及同學說,如果遇到來自於自己國家的學生,他們還是選擇用英文溝通,好像母語只是一種私領域的語言,那種無比親切感不適合「專業」的教學場合。當時我不同意這樣的觀點,覺得這不是一種自我矮化、自我殖民嗎?好像講英文代表「高尚」、「國際化」。後來開始教高年級的商業寫作與技術寫作課,班上偶爾有幾位中國或香港的學生(目前還沒遇過台灣的學生),我的確有過兩個學生因為知道我會說中文而想要拉近關係、佔便宜,我也才了解當初的老師及同學為什麼那麼說。但同時我也擔心,難道同樣是東亞人、會說中文,就代表我們不能彼此尊重嗎?難道我們只能尊重白人教授,不能尊重東亞或是其他人種的女教授、女老師嗎?
這幾年時常對各種種族、性別、性樣議題反思,而一間寫作課的教室更會因為各種議題的討論深化這些標籤的(不)合理性。其實不只是在美國,我覺得世界各角落都有這些身份認同、標籤的議題,包括台灣。
我時常反省以前自己的保守傾向,安逸於體制內的生活,而沒有去反思我自己身為台灣漢人與原住民或是新移民的關係。而我也在台灣父權社會之下,學著當一個安靜順從的女人,我也許曾有許多不解與痛苦,但我沒有試著用我能理解的語言去表達,為各種不公義發聲。我時常對自己遲來的質疑感到懊惱,希望用生命中剩下的時光去探索、反思,透過教學、研究與寫作提出異議。
教寫作課的時候,我很喜歡讓我的學生們接觸不同群體所產出的文化與文本,過去這學期教技術寫作課更是如此。那是一個非常「白」的班級,班上除了一個黑人,一個亞裔美國人,三個中國人,加上他們的老師以外,都是白人,而白人男性又佔絕大多數。那是一個一開始讓我非常感到不安的班級,雖然已經在教學場合看習慣了白種男人的優越感,對自己的教學也很有把握,我還是會害怕。
但我還是很想藉由這個機會,慢慢傳達一些理念,尤其想要顛覆一般人認為技術文件都是科學公正的看法。我們於是討論了美國政府官方文件對於美國原住民的描寫,文件本身不但移除了原住民的觀點,也磨滅了殖民與屠殺的歷史。我們也討論為什麼蘋果的Siri和亞馬遜的Alexa都是使用女聲,班上一位天真可愛的白人男孩David說:「因為女人的聲音比較具有安撫鎮定的作用。」當時班上沒有其他人接他的話,我說:「也許吧。但身為一個女人,我替我自己和我們班上在場的七位女性感到悲哀。」
這個暑假第一次不在英文系裡教課,在談論女性、性別、性向的課堂裡,我有一群對「多元性」這個概念非常好奇的學生,組成有許多黑人、拉丁美洲裔、波多黎各人、印度人、中國人、香港人、白人,其中女生佔多數。
我自己對於「多元文化」沒有什麼太浪漫的想像,因為表面的多元和諧大多數是主流文化壓迫少數族群的結果。我想起小學社會課學「九族」文化,我們好像是從一種殖民的人類學家視角,背誦他們的節慶習俗,而不是真誠地去了解原住民的故事與世界觀;就像我們一方面幫新移民貼標籤,說人家不是「泰勞」就是「菲傭」,好像他們不是人一樣,然後再說台灣的文化很多元。
在教室裡看著彼此、談論多元何等困難。因為那不只是要看見族群的組成不同,還要意識到自己在這樣的社會體制中,被賦予多少特權,並且去傾聽、承認那些受傷的人的經驗。光是做到傾聽還不夠,更理想的是去明白,自己如何在這個體制成為共犯。而特權就像空氣一樣,我們依附著它卻不願意去思考探觸它的存在。說著說著,我只想到我自己,學界與教育何嘗不是一種特權,我想知道社會如何容忍一群沒有什麼「實質產出」,卻拿著筆針砭事務的異議者。
其實四、五年前的我不知道原來我會走上教學與研究的路,但我一直以來都很幸運地碰到很好的人師,尤其我的國中班導莊慧珍老師、高中國文老師朱美卿、大學的歐茵西教授 、胥嘉陵教授 、黃山耘教授、張則周教授 、盧桂珍教授 ,還有在交換時期遇到的 Professors Jon Thompson 和 Allen Stein,當然還有在研究所裡一直啟發我、引領我的老師們。在這些老師們的課堂中,我都被溫柔、寬和地對待著,他們讓我看見知識溫暖的力量,也不忘提醒我知識被濫用時是如何成為殺人工具。
雖然我對各種身份的標籤與隨之而來的特權與不平等非常敏感,但面對學生心理總有自己無法隱藏的溫柔,大多時候我替他們能夠擁有的未來心喜,希望他們未來遇到的人待他們好,但我也知道有些人的人生會因為這個不平等的世界而比他人辛苦。
而我也不再是那個22歲剛開始教書的單純年歲了,學術與專業的累積很容易把一個人年少的青春與單純消磨掉,但我還是想把自己簡單執著的一面保留下來,留給課堂,教學相長。
剛才學生回信說,「張老師,謝謝妳的幫忙,妳對我真好。」
不客氣,有你們真好。